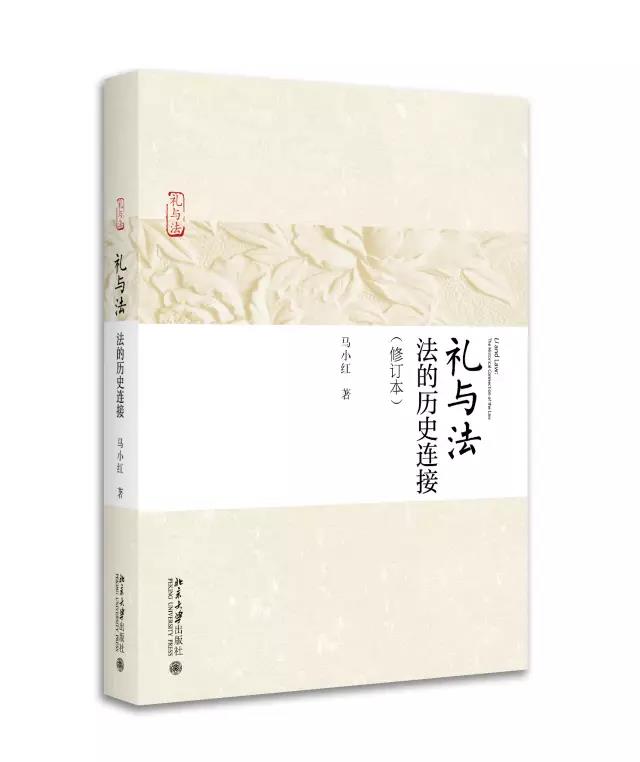马小红:“古代法”是已静止了的过去,而“传统法”则是一代又一代人对古代法的阐释
法的发展规律与发展模式是法学研究中最为基础的问题,在人类发展史上,基于人类社会的共性,法的产生和发展当然也有普遍的规律。 中国古代法作为法的一种类型,在发展中与西方法有“同”与“不同”之处。比如其在发展过程中也依次经历了神判法时代、习惯法时代和法典时代。但在不同时代中国法律的表现形式和内容与西方不尽相同。 英国法学家梅因对法典形成初期的古代法律的普遍表现形式是这样归纳的: 这些东方的和西方的法典的遗迹,也都明显地证明不管它们的主要性质是如何的不同,它们中间都夹杂着宗教的、民事的以及仅仅是道德的各种命令。 显然,中国古代法在发展伊始也未能例外。 梅因在总结西方社会法的发展规律时又言: 所有进步社会的运动在有一点上是一致的。在运动发展的过程中,其特点是家族依附的逐渐消灭以及代之而起的个人义务的增长。“个人”不断地代替了“家族”,成为民事法律所考虑的单位。 百余年来,我们的研究一直在中西文化的比较中进行。而比较的基调,又将中国传统文化始终放在弱势地位。所以对中国古代法的一些独到之处,我们常常受西方学者的影响而给予消极的评价。 受梅因的影响,我们对中国古代法中缺乏发达的民事法律制度而深感自卑。但实际上我们不仅从古代的乡规民约、家族法和禁忌中可以看到大量的相当于今天民事法律性质的“细事”规则,即使在国家制定颁行的法律中也不乏“一切公民间的关系上”的法律。孟德斯鸠这样定义民法:“人类在一切公民间的关系上也有法律,这就是民法。”土地、房屋及一切物品的租赁、典当、买卖等规定是中国古代法有机的组成部分。在中国古代租赁、典当、买卖契约的签定除交易双方外,还必须有“保人”的画押、签字。以双方自愿、平等为原则产生的契约(起码形式上如此)具有法律的约束力,一旦双方产生纠纷,契约就是官府判断是非曲直的法律依据。可以说中国古代不存在“民法”“刑法”,也不存在着如今“走红”了的“民间法”“国家法”这种法律类型的划分,但这并不是说中国古代就没有类似近代民法性质的法律规则,中国古代就没有调整人与人之间关系的法规。只是中国古代社会法律的类型划分另有标准,比如从宏观上说礼与法,从法的体系上说汉代的律令科比、唐代的律令格式等。而这种划分的标准更符合当时中国社会的实际状况。 再比如孟德斯鸠这样评价中国法律: 在中国,腐败的统治很快便受到惩罚。这是事物的性质自然的结果。人口这样众多,如果生计困乏便会突然发生纷乱。中国的皇帝所感悟到的和我们的君主不同。我们的君主感到,如果他统治得不好的话,则来世的幸福少,今生的权力和财富也要少。但是中国的皇帝知道,如果他统治得不好的话,就要丧失他的帝国和生命。中国虽然有弃婴的事情,但是它的人口却天天在增加,所以需要有辛勤的劳动,使土地的生产足以维持人民的生活。这需要有政府的极大注意。政府要时时刻刻关心,使每一个人都能够劳动而不必害怕别人夺取他的劳苦所得。 所以这个政府与其说是管理民政,毋宁说是管理家政。这就是人们时常谈论的中国的那些典章制度的由来。人们曾经想使法律和专制并行,但是任何东西和专制主义联系起来,便失掉了自己的力量。中国的专制主义,在祸患无穷的压力之下,虽然曾经愿意给自己带上锁链,但都徒劳无益;它用自己的锁链武装了自己,而变得更为凶暴。因此中国是一个专制的国家,它的原则是恐怖。 孟德斯鸠的这些有关中国法的论述对中国传统法的研究可谓影响深远。 其实,在丰富的中国古代法的资料中,否定这些“定论”和“通说”的例证我们可以信手拈来。中国古代的县衙州府的公堂之上,官的意志并不能决定一切,皇帝更不是可以凌驾于法律之上而为所欲为的。事实上,古代法律在为官治民提供依据的同时,也为被冤之民保护自己提供了渠道。起码自秦时起就有称为“读鞠”“乞鞠”的上诉制度,在一定程度上约束了官员的枉法或用法不当。如果上诉失败,人们甚至可以通过击“登闻鼓”、告御状的形式为自己讨一个说法。 中国古代的立法也绝不像有些人所认为的那样随意、简陋。唐代武则天时发生过一件著名的徐元庆复仇案。武则天赞赏徐元庆为父复仇之举,主张免其死罪,改判流放。谏官陈子昂在分析了案情后主张对徐元庆先处以死刑“以正国法”,再树碑立坊“旌其闾墓”以表彰孝道。最终,陈子昂的主张被采纳。这一案例一百年后又被柳宗元提起重新剖析。可见古人对法律的制定与执行都十分慎重。皇帝及各级官吏,只要想维系自己的统治并治理好国家,就不应该也不能为所欲为。 此外,中国古代法也不是如有些学者所认为的只是缺乏精神的条文堆砌。而自成体系的、完备的法律不会只是古人的随意之作。保留于中国与日本的300余部中国古代律学著作足以使中国古代没有法学的观点不攻自破。另外在律学的资料中我们所看到的情况是:关注法的最终价值的实现正是中国古代法的典型特征。中国古代法的价值体现于对道德理想的追求中。换句话说,道德是法律的精神和灵魂。法条也好,裁判也罢,只有在不背离道德的情况下法律才能得到普遍的认同。相反,法律若违背了道德就会引起人们的非议,甚至是来自执法者自身的抵触。中国古代法的法网不可谓不密,但对孝子、列女、侠客、义士却常常网开一面,这种表面看起来的“曲法”之举,目的则是追求法制背后的法之精神的实现。 由此看来,这样的理解也许更合理:中国古代法的发展在表现出法的一般发展规律的同时,还有其特殊的发展规律,其形成了与中国古代社会的自然环境、文化背景相辅相成的法的模式。西方法也是如此。法的发展模式过去不是、现在与将来也不应该是唯一的。 中西方法的诸多差异并非是绝然对立的,相反在一定的条件下两者是可以互补的,比如中法强调人们的自律,西法则重视制度的制约;中法重实体,西法重程序;中法在礼教的文化背景下视法律为维护道德之器,故而形成道德信仰,西法在宗教气氛的熏陶下养成法律至上的法治信念。在中国传统的观念中,法的追求目标是社会的和谐,法的核心源自符合人类天性的“人情”;而西方始终将利益的平衡作为法所追求的正义目标,法的核心是维护人们与生俱来的“权利”。在立法上,中法重经验,强调法是由“人”制定、由“人”施行的;而西法重学理,强调对法的服从和法律形式的完善。在法的实施中,中法重变通以尽人情,同时格外注重对法的负作用加以限制;而西法重规范以示公平,同时格外用力发挥法的积极作用。不一而足。而这些差异的形成在交通不畅、信息不通、相对封闭的古代是理所当然的,而梅因及孟德斯鸠所认为西方法是促进社会进步的动力,而东方法是制约社会发展的障碍及西方法优于世界其他地区和国家的法则完全是一种偏见。因为中西方古代法的差异根本无优与劣、先进与落后之分,所有的只是环境与历史所赐的“不同”而已。而在法的未来发展中,中西方古代法中的精华都可以作为现代法的营养而被汲取。 百余年来,尤其是近20年来,古代法在中国常常被作为法治发展的绊脚石而受到责难,长期以来若要对古代法作一些实事求是的肯定,实在是一件十分困难的事。困难的原因在于我们已经习惯了用别人的标准评判自己,习惯了用批判取代研究。本书所欲解决的问题缘于这样一个想法:21世纪我们应该而且必须摆脱以往“习惯”与“成见”的束缚,在研究古代法的同时,应该反省我们对待历史与传统的态度,反省我们在研究中所持有的标准、所运用的方法。只有如此,我们才能更准确、更合理、更学术化地解读中国古代法,才能在解读古代法的同时构建对现实有着积极作用的传统法并树立起应有的对未来的自信。
——节选自《礼与法:法的历史连接》(修订本)引言